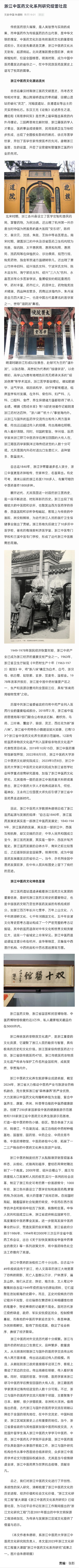
原文链接:https://share.ccmapp.cn/shareDetail?1=1&action=opendetail%3Brichtext%3B6810add556be8b58b01a16d1&siteId=2
原文如下:
浙江中医药文化系列研究绽蕾吐蕊
朱德明
传统医药悠久璀璨,是人类智慧与实践的成果,而中医药作为传统医药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医药文化则是传统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先秦还是汉唐,浙江中医药文化从无到有,起源绵延。北宋逐渐跃居全国前茅,南宋辉煌灿烂,位居全国榜首。明清时期,成为中国中医药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在中华民族医药发展史上谱写了悦耳的篇章。
浙江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自古迄秦汉时期浙江医药文献匮乏,而考古文物相对丰富,萧山跨湖桥遗址的草药罐,田螺山遗址的碳化“灵芝”,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等出土的芡实药物化石。东汉王充《论衡》论述养生之道,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系统的内外丹理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籍医药学人才辈出,医药事业成绩斐然,民间医药卫生习俗初步形成,出现了全国极有影响的姚氏、徐氏等医学世家,开创了医学世家传授医术的先河。唐朝浙江医官、生的设置,开启了设官建制管理浙江医药行业的先河。

北宋时期,浙江各州县设立了医学官制和惠民药局,掌管药物,为民治病。还出现了杭州第一所亦是当时中国为民服务的最大医院“安乐坊”,陈师文、裴宗元、沈括、朱肱、王执中等名医辈出。南宋时期,建置浙江的中央及该省医药卫生机构较为完善,御药院、太平惠民局、惠民和剂局、惠民局、施药局等在体恤民众、诊治疾病、规范行规、炮炙药物、施舍军民诸方面建树非凡。还出现了萧山竹林寺妇科、绍兴钱氏女科、宁波宋氏女科、陈木扇女科、海宁郭氏女科、绍兴“三六九”伤科、永嘉医派等众多医家学派。蛰居临安的朝廷重视药学,药材丰富,药市红火,药店林立,药物炮炙技术精湛,药品种类繁多,药商远涉海内外。朱丹溪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世称“滋阴派”鼻祖。

明清时期浙江形成以张景岳、赴献可为主的“温补派”,以张志聪、高世栻为代表的“钱塘学派”,以俞根初、高学山为首有地域色彩而无师承关系的“绍派伤寒”等学术流派。浙江医学基础理论,诸如脏腑学、运气学说、病因病机学、诊疗学都有嬗进,临床医学有所发展,在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儿科、口腔科、食疗、养生保健诸方面都取得了骄人业绩。根据《图经本草》等15部史地著作记载明清浙江药材达百种,“浙八味”“杭十八”享誉海内外。从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传出和传入两方面来看,传出远远超过传入的规模。传出高峰在明朝,传入看好清朝。同时,邻国的官医、学问僧、医药学家来浙江研习中医药学后携宝回国的大有人在,浙江籍医药学家飘洋过海传经送宝的人数十分可观。尤其是国内外药材进出口生意红火、品种繁多、数量庞大。
自古迄1840年,浙江孕育着诸多名人贤士,浙江中医更是衣钵相传,世家林立,名医辈出。有史可考,清末以前的浙江名医1700多人,有案可稽的中医药著作1800多种。
翻开近代、尤其民国这一时段的浙江医药史,是一段不断改进、时刻革新的历史。浙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中医院和诊所,也散发出西方医药学的芬香,西医医院和诊所争相崛起,客观上与传统的中医院、所交相辉映,为近代浙江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了贡献。浙江各地先后建立了10多所中医学校,著名的有瑞安利济医学堂、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和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形成了近代浙江中医教育的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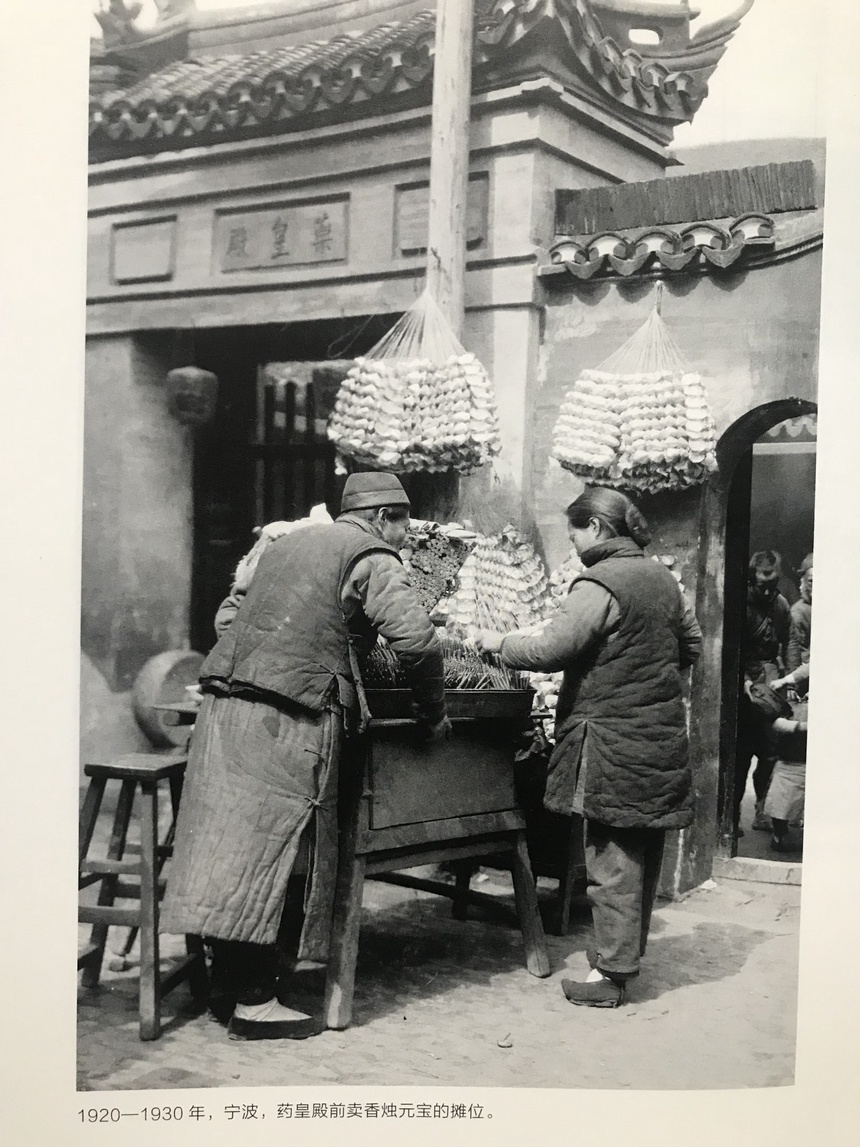
1949-1978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浙江中药产业已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1963年,浙江省卫生厅制定《中药材生产十年(1963-1972)规划》中,将“浙八味”确定为白术、白芍、浙贝母、杭白菊、延胡索、玄参、笕麦冬、温郁金。1978年改革开放后,浙江是中国中药材重要产区之一,生产和资源总量均列全国前三位,具有“东南药用植物宝库”之称。
历届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均将中药产业列入医药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2 月,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等7部门联合公布铁皮石斛、衢枳壳、乌药、三叶青、覆盆子、前胡、灵芝、西红花为新“浙八味”。浙江省中药特色小镇建设如火如荼,已有133个浙江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12项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9年10月15日,浙江中医药博物馆新馆开馆;2022年8月5日,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成立;2023年3月8日,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成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育研究基地,加强了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中医药重大科研成果叠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才培养成就非凡,何任、葛琳仪、王永均三位国医大师先后引领了浙江省中医药界走进新时代。
因此,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朱德明总结了浙江医药起源与发展的规律:“自古迄1840年,浙江医药发展史其实是一部浙江中医药发展史;1840-1949年,浙江医药的发展,其实是一部浙江中、西医互相抗衡,却又交融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浙江医药发展,其实是一部中、西医并驾齐驱史。浙江医药发展的总体水平,南宋之前比较落后,之后逐渐跃居全国前茅。明清时期,成为中国医药发展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当今,亦名列全国中医药发展前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留下了绚烂的足迹。
浙江中医药文化特色显著
浙江医药遗址遗迹承载着浙江医药文化发展的重要信息,是研究浙江医药文明史的重要物证,也是中国医药文明乃至世界医药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浙江百万年长兴七里亭、万年上山文化、八千年跨湖桥文化、七千年河姆渡文化、五千年良渚文化等史前考古遗址构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考古证据链,其中的医药遗存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贡献巨大,这在一个省域史上非常罕见。浙江中医药遗迹遗址主要分布在杭州、金华等地区,云集在中西医疗机构、中西药房和中西名医故居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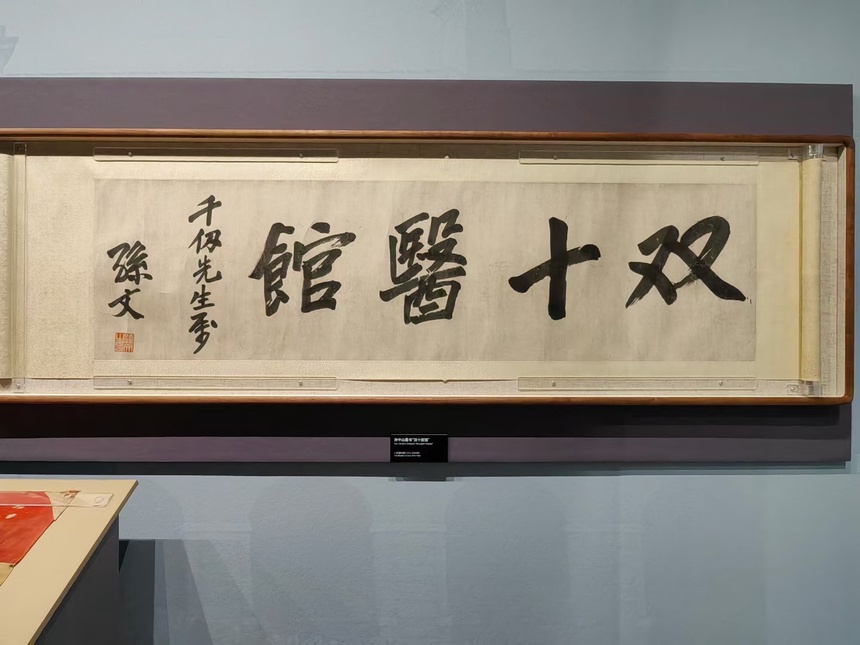
浙江医药文物,浙江省国营和民营博物馆、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约达3万件,私人藏家相关藏品约在5000件内。
浙江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浙江重要的文化资源,它凝聚了浙江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浙江国家级传统医药达12项,浙江省级传统医药47项,浙江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名列全国前列,成就斐然,享誉海内外。
浙江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事业成就卓越,截至2024年,浙江省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与旅游业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浙江省“森林康养”的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以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体验为主题,复合中医养生、康复、休闲、科普等功能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创建了250多家国家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和133家浙江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打造一批中医药特色小镇、街区。整合串连了大运河、钱塘江、千岛湖流域、瓯江沿线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国医馆、国药馆、中药企业、中药交易市场、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体验中心等,拓展了一二三产融合的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产业链。
浙江中医药制度经历了从酝酿萌芽到呈现基本样态,从细化、式微再到循序,曾经在两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度。2000年前,绍兴会稽山下,越王勾践重视人口发展和人民的疾苦,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制定了浙江有史可考的第一份医政敇令;1000年前,浙江各州县设立了医学官制和惠民药局,掌管药物,为民治病,极大的普惠了民间百姓。自民国时期起,随着国家社会制度的转变,中医药在西方医学的冲击和影响中经历了探索、转换和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浙江省政府响应国家号召,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营造发展的良好氛围,浙江省政府分别于1986年、1994年和2000年三次召开全省中医药工作会议,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我省中医中药事业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将中医药特色化立法工作推向了高潮。
浙江中医药防治疫疠工作十分出色。自古迄1949年疫病流传于浙江,给人文荟萃的浙江大地笼罩了恐怖的阴影,死亡人畜数以万计,尸体漂浮,遍及山野。我们从正史、野史、地方志、文人笔记中搜集到自古迄1949年疫疠流行的原始资料,它们星散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而且,正史对疫病流行的记载并不完整,往往镶嵌在赞颂帝王将相蠲恤功绩的笔墨中,野史稗乘的记载更不周全。面对历代浙江疫疠肆虐,政府、军队安抚疫区民众,控制疫情蔓延,而各地的中医药学家追古发今、各显神通,为民排难解忧,取得了防疫成就,稳定了社会秩序,赓续了经济繁荣。
浙江中医药对外交流历代都十分频繁。浙江与国外的药材进出口生意红火、品种繁多、数量庞大。从元明清时期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传出和传入两方面来看,传出远远超过传入的规模。而且,从朝廷到浙江政府直接插手这项工作,客观上推动了双边的交往。传出高峰在明朝,传入看好清朝。同时,邻国的官医、学问僧、医药学家来浙江研习中医药学后携宝回国的大有人在,浙江籍医药学家漂洋过海传经送宝的人数十分可观。不过,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只局限于邻国,主要聚集于日本、朝鲜,很少涉猎欧美、非洲和大洋洲。值得指出的是,古代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在明朝以降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在中外交流史、中国科技史、浙江区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今,浙江省委省政府与其他国家加强中医药科技交流,大批国外留学生涌入浙江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药、中药,浙江中医药孔子学院开设多国,浙江中医药医疗队奔赴国外从事医疗救助工作,浙江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众多浙江中医药学术论文刊登国际权威杂志,尤其是当今疫情肆虐全球,浙江中医药界为世界抗击疫情,贡献非凡。
总之,我们对浙江中医药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系统性的深入研究,清晰梳理了浙江中医药文化的历史进程、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课题《浙江中医药文化系列研究》已绽蕾吐蕊,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乃至2001年提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添砖加瓦,为传承与发展浙江区域文化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本文作者朱德明,系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负责人,本文是2023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课题“浙江中医药文化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图片由朱德明摄)

 企业微信号
企业微信号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